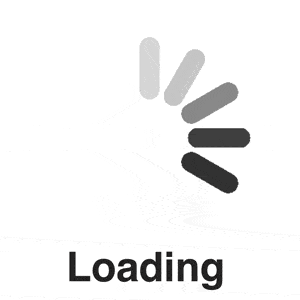8月11日消息,据国外媒体报道,《新共和》是1914年创刊的百年老店,带上自由派色彩的《新共和》是全美话语权力极高的“意见杂志”,堪称美国自由主义的舆论旗舰。然而巨轮也在遭遇互联网基因带来的巨大冲击

8月11日消息,据国外媒体报道,《新共和》是1914年创刊的百年老店,带上自由派色彩的《新共和》是全美话语权力极高的“意见杂志”,堪称美国自由主义的舆论旗舰。然而巨轮也在遭遇互联网基因带来的巨大冲击。日前,美国《大西洋月刊》刊发了首席编辑Franklin Foer的文章,这位德高望重的《新共和》老编辑指出,在互联网大潮之下,媒体业已经丧失了新闻独立性,新兴媒体普遍以用户流量为中心,新闻不断被科技侵蚀,已经成为数据的副产品。Facebook联合创始人克里斯掌管下的《新共和》也难逃这种厄运。
我在《新共和》杂志的整个职业生涯中,一直在梦想着这样一个恩人。多年来,我的同事和我一直穿梭于互联网时代,接触了无数的公司。虽然每一个都渴望拯救我们的杂志,但不是因为资源匮乏,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信心导致功亏一篑。无休止的寻找终究耗尽了我们所有的精力, 2010年,我辞去杂志编辑的职务。
2012年,克里斯加入了进来。对于我们来说,克里斯不只是一个救世主,也是互联网时代精神的代表。在哈佛,他与马克・扎克伯格(Mark Zuckerberg)是同寝好友,已经成为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之一。对于我们的杂志,克里斯带来了更多的时代精髓,更多的预算开支,更重要的是其作为内部人士,带来更多关于社交媒体的丰富知识。我们感觉新闻业的希望全部仰仗于此,由此所做的一切也似乎令人陶醉。《新共和》杂志似乎成为了新闻业依赖于硅谷的代表。
在早春的一个平常一天,克里斯向我抛出了橄榄枝。我们手中端着纸杯咖啡,在华盛顿市区漫步聊天。在刚刚收购《新共和》杂志的第一个星期,克里斯重复了多次这种形式的交谈。他似乎渴望与曾为杂志工作过的任何人、或者对杂志有强烈看法的任何人交流。当我们交谈时,我意识到他不仅仅是要我的一些建议,开始怀疑他想让我重回《新共和》的编辑岗位。不久之后,他给了我这份工作,我欣然接受。
根据我的从业经验,《新共和》的老板该是财务自由,观点老道的中老年男子。但克里斯有所不同。他才28岁,充沛的学习热情使他看起来更加年轻。在蜜月期间他在读《战争与和平》,他的SoHo公寓里堆满了文学杂志。“当我第一次听到《新共和》要转手时“,他告诉我,”我去了纽约公立图书馆,开始了解这本杂志。“当他看到关于《新共和》杂志的胶片简介,读到杂志历史和相关作家的浪漫,其中不乏丽贝卡・韦斯特(Dame Rebecca West),弗吉尼亚?伍尔夫(Virginia Woolf),埃德蒙・威尔逊(Edmund Wilson),拉尔夫・埃里森(Ralph Ellison)以及詹姆斯・伍德(James Wood)等名流大噶,这一切让他解开了自己的钱袋。
即便Facebook的上市带给克里斯数亿美元的财富,他似乎对他的钱无动于衷。当人们论及他的不动产,他会面红耳赤。他的财富来源并没有让他有成就感,实际上他总是以旁观者的角度谈及Facebook。在晚餐时他曾向我承认,并没有太多依赖于Facebook。很快我们开始着手重塑杂志,期望实现我们自己不可思议的价值。
在过去的时间里,新闻业在不断被侵蚀。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媒体公司,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码字传统的继承人。有些人喜欢把自己的公司与技术公司进行类比。而这种对媒体公司的重新定义不仅仅是一种时尚。随着硅谷的逐步渗透,新闻业已经依赖于大型科技公司,后者目前现在为新闻业提供了很大一部分受众群体,因此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。
依赖产生了一种绝望――通过Facebook对点击率的疯狂追逐,对谷歌搜索算法的深究细扣。媒体与科技公司牢牢绑在一起,他们给予Facebook发布广告的权利,或允许Google通过其快速加载服务器上直接发布文章。
更可怕的是科技公司往往反复无常,其经常对策略进行反复调整。 比如Facebook认为用户喜欢视频甚于文字,因此它将不再强调新闻流中的文字或硬新闻。当其进行这样的策略转换,或者当谷歌调整了搜索算法时,相关媒体的用户流量可能会随之下降,导致收入出现波动。然而问题不仅仅是收入的脆弱性。科技公司的影响力可以影响整个媒体行业的精神,降低质量标准和侵蚀行业道德。
我从未想过我们的杂志也会这样走下去。我和克里斯一起工作的第一天令人兴奋。作为一个局外人,他没有兴趣盲从常识。当我们开始重建《新共和》的网站时,并没有以引流为主导,不会以提高点击率为目的设计主页。我们的数字页面以美观简洁为主旨,同时保存长篇新闻和严肃文化特色。
克里斯一再强调,他相信自己可以把《新共和》变成有利可图的公司。但他对利润的言辞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真诚。 “我讨厌销售广告,”他会一再告诉我。 “这让我感觉很幼稚”。入主《新共和》一年多以来,他似乎放弃了营收。但事后看,我可能会更加审慎地对待我们自己。我们都有着不少弱点,他在黄金地段租赁办公室、雇用顶级顾问,而我为优秀作家走遍全球、慷慨付款。克里斯好像对此并不介意,“我从来没有过这么高兴或满足过,”他会告诉我,“我在和朋友在一起工作。”
不过最终,这些数字还是找上了克里斯。钱需要来源,而这个来源就是网络。终归流量的急剧增长才能带来所需的营收。所以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突然放弃了原有的基调。

本世纪初,新闻业处于极端变化当中。经济衰退加上读者千变万化的阅读习惯,迫使媒体公司面对数字化未来不断进行赌博。十多年来,报社员工人数下降了38%。随着新闻行业的不断萎缩,其声望应声大跌。一份报告称报纸记者是美国最糟糕的工作。这个行业发现自己不得不重新考虑生存问题。媒体独立一夜之间似乎成了完全不可负担的奢侈品。
用户流量的增长需要一种新的心态。曾经纸媒与电视完全不同,从不会把受众需求当作企业主旨。《新共和》更是持有这种信仰的极端媒体。问世百年来,这本杂志成了美国自由主义的舆论旗舰,有着一个忠实的读者群体。然而,在杂志创办的漫长历史中,这样一个读者群体甚至还无法填满密西西比大学的足球场。
在互联网时代,一个更大的读者群体显然触手可及。很多媒体公司已经汲取了这个经验,BuzzFeed的创始人约拿・佩雷蒂(Jonah Peretti)就这么说:R =?z。 (在流行病学中,?表示传播的概率; z是暴露于传染性个体的人数)。这个方程式说明了一段内容可能如何进行病毒式传播。但是,虽然佩雷蒂从流行病学中得出了他的传播公式,但新兴的流量问题是真正行为科学的一个分支:人们点击这么快,他们并不总是完全明白为什么。这些点击都是在半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的,受到认知偏见的影响。也就是说,读者总需要一点点背后的操纵。
克里斯不仅对引流的必要性日益重视,也知道增加用户流量的技巧。克里斯自己就是数字媒体小组的成员,他从Upworthy了解到病毒式传播的方法,而后者正是一家克里斯给予资金支持的网站。该网站从互联网上抓取高频视频和图形,然后从中注入引流元素,使它们变成病毒。正如心理学家所知道的那样,人类对无知感到舒服,但是他们却排斥信息。 Upworthy使用这种心理学上的洞察力开创了一种标题风格,明确地挑逗读者,只留下少量信息来吸引他们点击阅读。对于发布的每个项目,Upworthy都会创作25个不同的标题,放在网上进行点击测试,从而确定最有效的一个。基于这些结果,Upworthy创作出高点击率的标题组合模式。比如这样的经典例子:“十分之九的美国人对迷幻事实的认识完全错误”和“你不会相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”。这些标题在网络上变得司空见惯,直到读者对它们有了免疫力。
Upworthy,BuzzFeed,Vox Media以及其他新兴的互联网巨头的核心观点在于,只要认真研究数据,就可以打造出编辑化的成功。这种观念已被整个媒体行业所接受,《新共和》也未能幸免。克里斯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装了一个数据库,以增加我们生产病毒性传播文章的概率。他密切关注着Facebook的实时热门话题,以及前几年在同一时间段内的热点内容。 “超级碗广告很热,”他在一次周例会上告诉工作人员, “我们可以借势创作点什么?”这样的问题通常带来了敌对的沉默。
虽然我对这种战术不以为然,但我也没有表示出强烈反对。克里斯仍然鼓励我们发表深度解析的长篇文章。更重要的是,他问了一个完全合理的问题:我们真的认为我们的杂志要比《时代》或《华盛顿邮报》这样的严肃媒体做得更好吗?如果只有我们能够自我约束,写出优秀作品,无疑点击率会快速提高。因为它有效,所以其他严肃媒体也都在这样做。我们需要脚踏实地的工作。
然而,流量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在《新共和》的工作。每次在办公桌前坐下来,我还是在偷偷关注流量。当我早上醒来时,当我站在镜子前,当我站在小便池前时,莫不如此。有时候,我只是盯着流量的上涨,却忽视了正在编辑的文章,忽视了坐在我身边的人。
我的主人成了Chartbeat,这是一个为作家,编辑和老板提供网络流量实时统计的网站,能够显示出每篇文章的活跃读者数量。 Chartbeat及其竞争对手几乎应用在每个杂志,每张报纸和每篇博客上。使用这些统计工具,作者能够通过随时改进提高点击率――更好的标题,更好的社会媒体平台,更好的主题,更好的论据。像一位经理站在装备线上的秒表,Chartbeat如同生产线旁的秒表,时时刻刻为新闻编辑室敲着警钟。
这是一个危险的转折。从本质上讲,媒体可能永远不会像编辑和作家所认为的那样有公德心。然而这种神话非常重要。它推动新闻从业者挑战权力,让记者唯我独尊,让媒体人高高在上、自以为是。在互联网时代,新一代媒体巨头对这种旧式的独立精神没有太多耐心。对于新闻业,这些公司并非没有伟大的理想。BuzzFeed,Vice以及《赫芬顿邮报》等互联网媒体都创作出一流的作品。他们旗下一流的记者都创作出让人印象深刻的调查新闻。但追求用户流量依旧是他们的中心任务。互联网的无尽反馈循环塑造出他们的编辑模式,这决定了他们的精力所在。
一旦一个故事引发了公众关注,这些媒体就会以反复的愤怒来撰写主题,挤压主题,直到公众失去兴趣。比如有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典型例子――关于明尼苏达一位狩猎者在非洲杀死了一只名叫塞西尔的狮子,这一消息产生了大约320万个故事。几乎每个新闻媒体――甚至包括《纽约时报》和《纽约客》在内的知名媒体都试图从塞西尔那里获得一些用户流量。这需要媒体从业者不断发掘找到新的角度。Vox这样说:《吃鸡肉在道德上比杀死狮子塞西尔更糟》;BuzzFeed的标题是这样的,《心理学家称她与死后的塞西尔进行了对话》;而《大西洋月刊》指出,《从塞西尔到气候变化:愤怒的风暴更胜一筹》。
在某些方面,这只是一个旧式堆叠的数字增强版。但社交媒体放大了吸引公众参与的经济效益。带来的相关结果是高度衍生的。The Verge创始人约书亚・托波尔斯基(Joshua Topolsky)对这种内容的同质化表示悲哀:“一切看起来一样,读起来一样,所有媒体似乎是在吸引同样的眼球。”
唐纳德・特朗普是这个时代的典型。比起最近历史的任何其他时刻,他理解现在这个时代,媒体都需要向公众传播热点。即使媒体蔑视特朗普,但依旧把他打造成了一个合理的候选人,在这一点上他们别无选择,只能拥抱他、包装他、掩饰他。在数据为王的主旨下,关于特朗普的故事把持着头条位置,引来巨大的用户流量。特朗普开始只是塞西尔的狮子,最终却成为了美国总统。
克里斯和我曾经坐在华盛顿的早餐桌上,思考《新共和》的核心品质,我们将共同重新组建的《新共和》。虽然我们并没有这么明确地说出口,但无疑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共同点,一个可以相互团结起来的形容词。如果有白板,那么势必已经被我们的想法填满。“我们是理想主义者,”他最终这样说,“它将我们的传统往事与我们对解决问题的乐观态度联系在一起。”诚然,理想主义是一个叩开我心灵的词语,让我对重组《新共和》的前景感到不可思议的喜悦――“欣欣向荣。就是这样。”
我们对我们共同的理想主义充满理想。但从本质上讲,我对世界的看法是道德和浪漫的,而克里斯则是技术性的。他遵守规则,富有效率,善用组织图和生产力工具。在克里斯入手《新共和》二周年之际,他与我一起讨论了杂志的未来。在经历了几个月的下滑之后,他已经厌倦了。克里斯认为杂志需要更大的网络流量和更多的收入。 “为了拯救杂志,我们需要做出改变,”他如是指出。工程师和营销人员将在内容编辑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。他们会为我们的新闻内容增加酷炫,创新的功能,有助于这些新闻在公众面前脱颖而出。当然,这需要钱,而相应资金将从对长篇报道的经费中支出。克里斯明确告诉我,我们现在是一家科技公司。 (但休斯否认这个说法)我回答说:“听起来好像我并没有资格运作这种公司。”但克里斯向我保证说完全可以。
两个月后,我从一位同事口中得知,克里斯已经寻找我的替代者。在克里斯炒我鱿鱼之前,我主动辞职了,大多数杂志编辑人员也都退出。他们的理想主义决定了他们将会站到克里斯唯心主义的对立面。他们不想为一家遵从硅谷精神而非纯粹新闻的出版社工作。他们愿意关注Facebook,却不希望自己的工作被Facebook所左右。《新共和》的变化,正是硅谷取代新闻业的典型。
数据将新闻变成了一种商品,要投放市场,经历检验和校准。在新闻行业的光鲜之下,这个行业正在一点点地腐烂。现在每个任务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――文章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流量来证明投入合理?有时这种分析是明确而有目的,但在大多数情况下,它依旧是一种潜意识和嵌入式的委婉语。无论哪种方式,这是一种行文思路,导致编辑们会考虑内容是否会有“不值得的努力”,或者担心文章是否会“下沉”。新闻的受众可能比以前更多,但是关于新闻的思维却更加狭隘。(晗冰)
声明:本文内容来源自网络,文字、图片等素材版权属于原作者,平台转载素材出于传递更多信息,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与学习,切勿作为商业目的使用。如果侵害了您的合法权益,请您及时与我们联系,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!我们尊重版权,也致力于保护版权,站搜网感谢您的分享!